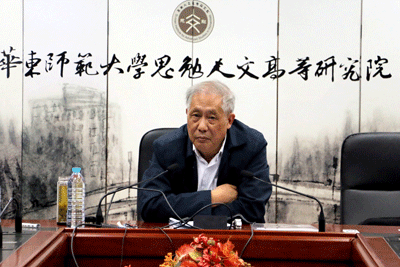
2017年11月15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国强先生在闵行校区5303学术报告厅,作题为“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的学术报告。该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报告会暨思勉高研院成立十周年高端人文讲坛第三讲,历史系刘昶教授主持、评论,思勉高研院、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上海社科院、复旦等校内外数十名师生参加。
“两头不到岸”一语,取自辛丑年(1901)梁启超于《清议报》中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梁公谈及中国之现状如驾一扁舟放于中流,可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杨国强先生引此言贯穿清末新政与民初共和困局,认为民初中国正是在一个个的变革中倾翻湮灭,在一个个的理想中颠沛失相,在两头不得到岸中走向的共和便成了名不副实的共和。再谈民初共和困局这个老题目,杨先生以独特的解读视野、宏大的叙事格局,将造成民初困局的内因上溯至清末新政中的变法更张,揭橥造成民初共和困局的内因理路,认为是清末新政中大刀阔斧的变革造成剧烈的震荡,又在剧烈的震荡中走向了局,而民国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经历剧烈震荡的烂摊子。报告中评说清末筹备立宪、各省谘议局、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洪宪帝制、丁巳复辟等重大政治事件,兼论清末民初党人、军阀、官僚、政客、知识人中身印时代烙印的重要历史人物。
首先,杨先生谈到“共和与一个分裂中国”的问题。武昌起义发难于清末新政中所培养的新军之中,而人物背后的地方谘议局,却在一开始便立于朝廷的对立之面,这个过程中的绅权扩张、地方主义蔓生使得地方与中央的裂罅节节扩大,而至国会请愿运动时达到高潮。共和正是在地方各省推举中、外人的干预下而建立。民初中国面对的深度矛盾,正是从前段历史的地方独立,渐变为共和之下的地方分裂,地方独立是由武力来表达,而独立又是由武力来维持,民初武人当政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给中国带来久苦的乱世。
其次,杨先生谈到“共和与一个社会解体的中国”的问题。清末新政中官制改革造成中国两千多年来官僚政治主体构成的大变,宪政编查馆成为筹备立宪的中枢,旧人物遭淘汰,新气象中的新人物层出不穷,却以不入流品的姿态进入到民国。新官制瓦解了政治结构,新人物改变了政治主体,自上而下的变革导致晚清留给民国的是一个社会解体的中国,原本礼俗之治下的地方社会结构发生裂变,绅与民关系日趋紧张,阶级矛盾恶化,就此引发的纲纪失常、社会失范表现为民初政治纷争、兵事迭起等一局不如一局的乱象。
接着,杨先生谈及“民初公共信条断裂”的问题。公共信条产生政治关系、人伦关系中的纲纪,纲纪者,天下之公义也。民初中国是抽象的、悬浮的、没有具体性的国家,纲纪不立、政治主体大变直接造成民初政治的士人化与武人的倒戈反复。士人政治在军阀与政客之间比比皆是,武人倒戈事变此起彼伏。在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忠义荡然无存,带有恩怨的个人成为国家意志的传达者与执行者。这个过程中暗杀四起,暗杀的可怕在于永远没有真相,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最后,杨先生谈及“移入的代议制走向山穷水尽”的问题,提出中国人对西方代议制的观察与认知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付诸实践则是在清末新政筹备立宪的过程之中,李鸿章、刘坤一、慈禧太后等相继谢世,庙堂失去政治重心,使得消长与重组的权力聚于亲贵之 手,亲贵无力担负筹备立宪的重责,地方一再请愿速开国会更是加速了自下而上的震荡。而当代议制度移入到实际的政治中时,构成代议制主体的约法、国会、政党均名不副实,其中包含的矛盾成为国人不能消受的东西,立法原当为天下之公器,而一变而为一方之重器、一派之利器。国会一度成为民初政议中常受訾议的题目。1912年初至1913年夏秋之交,一年半的时间立宪政治在民初中国便已走到尽头,名存而实亡矣。
刘昶教授对报告做了点评。他认为,杨先生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极富逻辑性的重新解读,提出历史研究需要“去熟悉化”,大量阅读史料,回归历史场景,获得更多独立思考。在场师生提出“宋案处理”、“民主共和思想在城市中的影响”、“纲纪维持”等问题,杨先生分别作答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