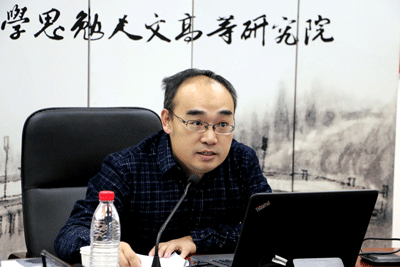
2017年11月24日下午15:00,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剑青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5303学术报告厅,作题为“‘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的学术报告,阐述了近期的研究成果。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春田老师主持、评论,共有思勉高研院、中文系、历史系等数十名师生参加。
季剑青老师将“声”乃至对“心声”的探求,作为鲁迅在生活早年的各个阶段一以贯之的追寻之物,层层递进,为我们阐明了这一意蕴的渊源脉络与复杂流变。
首先,季老师以早年鲁迅的翻译作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造人术》为例,提示我们应当关注鲁迅于1906年便开始发生转向,从关注借翻译以输入科学知识,转为借此关注人的心理状态。在1906年《造人术》的翻译之中,鲁迅以文言表现了近乎现代西方意识流手法的内心独白,这一类心理描写是传统白话所无法容纳的。除语言的特殊性外,《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有“籀读其心声”等言,其中“心声”一语,在鲁迅的概念范畴中已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心声截然有别,从道德状态的表征转为强调某种动作性与能动姿态。
为对此处“心声”作进一步溯源式的追寻,季老师绍介了章太炎的语言观,以体现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阐明当时鲁迅与章太炎存在某种内部逻辑的一致性。章太炎注重因声训而求本字,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博考方言,寻其本根。在他的语言观中,声音是文字之魂,繁多的本字与反复的声音,能够构建出一个“各有殊音,自抒其意”的生命世界,使得语言带上了生命属性,担当了“心思之帜”的身份角色。
在早年鲁迅的翻译实践中,实则体现了章太炎对语言的某些思考。木山英雄指出,《域外小说集》体现了翻译者将古字古意相对译的试验。在这部兄弟二人合译的作品集中,鲁迅仅翻译了三篇作品,其中《谩》与《默》均呈现了孤独个体的心声。但《域外小说集》共售出一二十部,这一借古奥的、字意一致的语言来表现“主观之内面精神”的试验,就外界的反应而言是失败了。藉由这一路径而表达“心声”,将难为众人所听见。季老师指出,在此时或许就埋下了鲁迅之后白话文写作的种子。
从翻译到创作,在20年代前后,鲁迅为“他人”的呐喊之时,选取了新式白话作为表现的语言,其出发点实在于其自身的切肤之感与渴切的应用需求。借古奥文字以表达“心声”的实践并不成功,而传统的程式化的白话在表现心理活动方面也仍有很大限制,与胡适等人意图直接汲取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白话文资源不同,鲁迅从新文化运动之始便在不断探寻足以传达“内面精神”的新式白话。在《狂人日记》之中,狂人以“负”的联系,达成了与他人的连带感。但作为作品中唯一较含暖色的人物——母亲,狂人也仍然并未能够进入母亲的内心,鲁迅意欲探寻的是,究竟如何能够通过人与人的联系,来发展新的实践的可能性,在此,新的语言或许能作为一道崭新通途,借以抵达新的前景。
季老师认为,前人的研究虽多有将鲁迅表述为体验的是“存在主义”的境遇,但其中仍存少许偏差。鲁迅在时时进行自我反思,考虑与他人的“连通”是否真正能够达成。斯皮瓦克曾批评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将民众吸纳整合到一个以欲望和利益的名义来建构自身的抽象主体中。鲁迅此处的思考,就使得他能在某种程度上绕开这一陷阱。他曾在30年代提出,要创作者不要将自己作大众的戏子,也不要将大众作自己的喽罗,只将自己作大众中的一个人。要以此来“发些较真的声音”。
但为发“较真的声音”,在实践上颇有难度。鲁迅往往为他人的伦理承担,压抑了自我表达的冲动。常常某一同人解体之时,鲁迅与他人的连带感削弱,才使其自我意识得以表露。在这一层面,《野草》便颇具典型性。鲁迅以戏剧化、情境化的手段,表达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借此表达方式,又将自身的自我意识对象化,呈现出向更广大的世界开放的可能性。“沉默”之时的“充实”,体现的是主体相对自足的丰盈状态,而因“开口”而感到“空虚”之时,便为这一状态消解的表征。这其中存在主体不断的分裂、挣扎和与他人繁杂的纠结冲突。如此的主体存在方式,彰显了鲁迅某种自我表达的困境。
最后,季剑青老师为我们做了总结,再次强调了鲁迅对表达“心声”的语言的追求,使其不断探索新式白话的可能。“为他人的伦理”已然成为鲁迅内化的意识指令,使鲁迅汲汲于对他人“心声”的探索与召唤。白话文仍存在未完成性,语言与心灵之间仍然难以达到透明关系。要注重“声”中所包含的生命感、能动性、主体性。
在季剑青老师的报告完成后,现场的同学纷纷提出问题,老师一一进行了回应,提出“进化论”等思想均预设了明确的方向,而鲁迅的所谓“中间物”更关注的是过程本身,在其思考中并无切实可抵的“终点”存在。鲁迅所思考并表达的主体性具有现代性,与文言中的“万物皆备于我”中,“我”作为“天”、“道”等形而上之具体表征不同,鲁迅的主体性更注重的是现代意义上基于个体的主体。
临近结束,张春田老师对报告做了点评。他补充道,章太炎的“革命”仍是在文明论意义上的“文”的革命,而鲁迅则进一步向下行,以现世的人的生存作为思考出发的基点,与季剑青老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